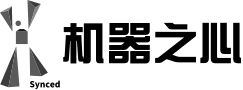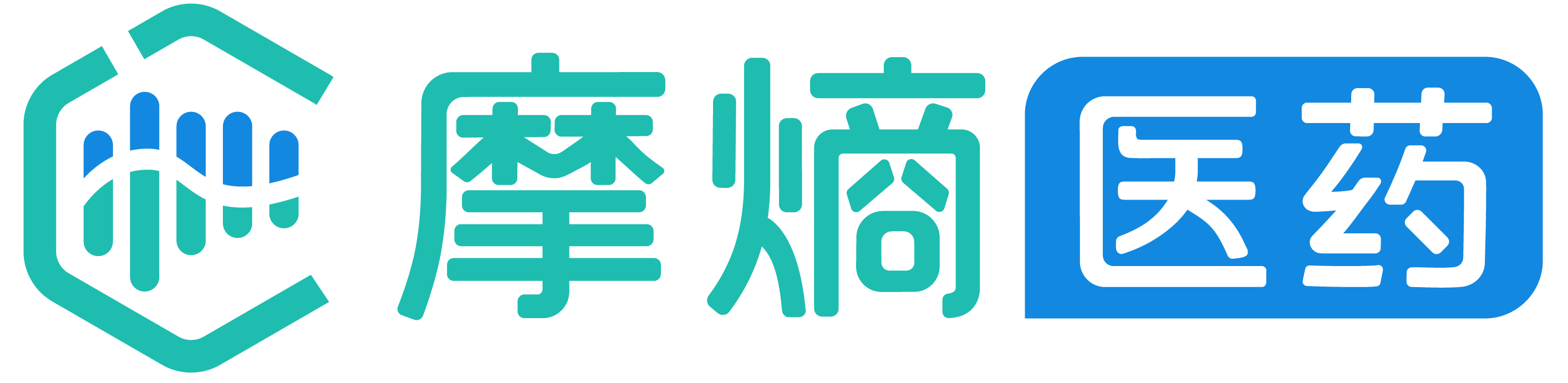一位生物学研究者,一位药物化学研究者,今天创新100人的访谈,围绕的是两位利用AI进行抗生素研发的教授。他们一个是不愿人类再次回到没有抗生素的黑暗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认为AI的加入一定能够加速抗生素研发的现实主义者。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里,我们讨论了抗生素研发的黄金时代,以及研发的断崖式下跌,也与他们一同回忆里在悉尼一间民宿里第一次通过AI生成里几十个看起来合理的化学式时的震撼,也聊到了他们从澳洲回到香港,希望立足中国但面向世界的研发梦想。他们的故事,从澳洲开始。
21 世纪初的一个午后,在位于澳洲的微生物研究实验室里,是杨小教授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命定时刻”。
那时她正专注于细菌转录过程的研究,与刚加入团队的马聪教授共同推进一项针对耐药菌靶点的关键实验——这是他们探索新型抗生素研发方向的早期尝试,涉及难度颇高的细菌蛋白活性验证。实验开始前,两人虽对方向充满信心,却也做好了反复调试的准备,毕竟在科研领域,“一次成功” 向来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当杨小教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实验样本的反应结果时,所有顾虑都烟消云散:目标细菌的活性被精准抑制,关键指标完全符合预期,甚至比预设效果更优。更令人惊喜的是,后续几次重复验证实验,无论是不同浓度的药物测试,还是与耐药菌株的对抗实验,结果都同样理想。
回忆起那一幕,杨小教授依然很激动。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仿佛是被选中的“命定之人”—— 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长期专注与方向正确的必然:“就该干这个!”
命运的指引并非第一次。在澳洲实验室的那次“命中注定” 之前,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早已在各自的人生轨迹里,与抗生素研发领域有着若即若离的交集—— 如同两条平行线,虽暂未交汇,却始终朝着 “解决人类健康难题” 的方向延伸。
杨小教授的科研起点,与微生物领域隔着一段“农学距离”。她本科与博士均就读于澳大利亚,最初钻研的是植物学,每天与作物生长规律、植物基因序列打交道。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爱挑战的人。” 谈及从植物学转向分子生物学的契机,杨小教授笑着说。彼时基因组学与微生物组学在农业领域的初步应用,让她亲眼见证了微观世界的科技力量如何颠覆传统研究模式,这种“用精密科学解决实际问题” 的魅力,让她在研究生阶段毅然转向分子生物学与结构生物学,从此一头扎进细菌转录过程的研究中。
事实证明,这份选择与她的科研天赋高度契合。进入微生物领域后,她的研究成果不断突破:博士期间,她发现了细菌RNA 聚合酶的一个关键亚基,这个基因位点以她名字的首字母 “杨” 命名为 rpoY,成为领域内对其学术能力的标志性认可;更难得的是,在澳大利亚研究员职位录取率仅百分之几的激烈竞争中,她博士毕业便成功获聘,为后续科研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马聪教授与抗生素研发的缘分,要从他在产业界的经历与海外求学的选择说起。上世纪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是中国医药行业以仿制药为主导的阶段,同时也暗藏着创新转型的萌芽。
作为药学专业的毕业生,马聪教授赶上了行业“药剂师缺口大” 的红利期,与同期许多同学一样,凭借专业背景轻松进入丽珠制药集团。彼时国内所谓的 “新药”,多是国外已上市药物的仿制,他的工作虽让他摸清了行业脉络,却也让他敏锐察觉到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 的行业短板。
“当时中国更需要的是‘从零到一’的早期开发能力,先能把新药设计合成出来,这个重要性优于后续的制剂创新。” 马聪教授回忆道。预感到创新药时代即将来临,而自己现有的知识储备难以支撑未来需求,他在进入产业界2 年后,果断决定重回校园深造。
“作为药学本科的学生申请美国的药学院,很多都侧重制剂或临床药理学,但我想从药物合成的源头突破,所以选择了法国。”2 年的产业经验让他明确了方向,最终赴法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又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继续化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为药物研发积累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功底。
就这样,一位从基础科研深耕细菌机制,一位从产业需求出发攻克药物合成,在波士顿的一间咖啡厅里,科学家杨小教授与“药剂师出身的化学家” 马聪教授相遇。彼时两人或许尚未完全预料到,两条看似不同的科研与成长之路,终将在“研发新型抗生素、对抗耐药菌” 的目标上交汇,共同开启一段注定不凡的事业 。
在人类与疾病抗争的漫长岁月中,抗生素是当之无愧的“生命防线”—— 它不仅终结了 “微小病原体肆意夺走生命” 的黑暗时代,更成为支撑现代医学体系的基石。
在显微镜尚未发明、人类未能窥见微生物真容的年代,面对肺结核、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人们只能归因于“神罚” 或 “瘴气”。即便 17 世纪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在显微镜下首次观察到细菌,提出 “微小生物可能与疾病相关” 的猜想,却因缺乏对抗手段,这些看不见的 “杀手” 依旧横行。
17 至 19 世纪的欧洲,外科手术因缺乏抗感染手段沦为 “生死赌局”:医生用未消毒的手术刀操作,术后伤口暴露在充满细菌的空气中,感染率高达 80% 以上。以至于21世纪的人们常常这样调侃甚至:在17世纪,若手指被剪刀划伤,医生会建议截肢;而截肢后,十有八九会因感染丧命。

显微镜之父列文虎克
据史料记载,拿破仑战争期间,因手术感染死亡的士兵数量,远超战场直接阵亡人数;19 世纪中叶,维也纳总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因产褥热感染导致的产妇死亡率一度超过 20%—— 这些悲剧的根源,皆因人类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
直到 20 世纪,抗生素的发现才彻底改写了这一命运。1928 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能抑制葡萄球菌生长,开启了抗生素时代;1941 年,青霉素真正投入临床应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挽救了数百万士兵的生命,美国甚至将其研制与原子弹开发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后,链霉素的问世攻克了肺结核这一 “白死病”,四环素、头孢菌素等相继诞生,将肺炎、脑膜炎、败血症等曾致命的感染性疾病,逐步变为可治愈的常见病。
数据更直观地印证了抗生素的价值:20 世纪 50 年代链霉素未广泛应用时,肺结核患者 5 年生存率不足20%,如今通过规范抗菌治疗,治愈率已可达 95% 以上。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平均寿命至少延长了 10 年,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发现”。
这些改变让现代医疗得以落地—— 从外科手术的术前预防感染,到癌症化疗患者的免疫力支撑,再到早产儿的感染防护,几乎所有医疗场景都离不开抗生素的 “保驾护航”。抗生素不仅治愈了疾病,更让人类敢去探索更复杂的医疗技术,它是现代医学的“基石”,也是人类对抗微生物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若说 20 世纪中叶是抗生素的 “黄金爆发期”,那此后的数十年,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领域便陷入了令人忧心的 “冰封期”—— 一面是全球 “限抗” 理念普及以遏制耐药菌,另一面却是新抗生素发现的断崖式下跌,甚至陷入 “归零” 的窘境。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范围内再没有全新作用机制、全新化学结构的抗生素类别问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葛兰素史克、罗氏等国际药企曾满怀信心地押注抗生素研发,试图复刻抗癌药的成功路径。彼时,制造业与生物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两大关键技术:一是“组合化学”,能通过自动化合成快速生成海量化合物库;二是 “高通量筛选”,可借助仪器设备对成千上万的化合物进行批量活性检测。这两项技术在抗癌药领域已大获成功 —— 如今临床上常用的多款激酶抑制剂,正是通过这种 “广撒网” 的方式被筛选出来。
然而,当这些成熟技术被移植到抗生素研发中时,却遭遇了“滑铁卢”。葛兰素史克在 2007 年《自然综述・药物发现》(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揭开了这场尝试的惨淡结局:该公司耗时十年,累计开展约 70 次高通量筛选(按 90 年代成本计算,单次筛选费用约 100 万美元,总投入近 7000 万美元),最终仅筛选出 5 个具备潜在活性的先导化合物,且没有一个能通过后续的临床前研究与临床试验,真正转化为可上市的抗生素。
这一结果清晰地证明,适用于抗癌药的研发逻辑,在抗生素领域完全“水土不服”。
利润驱动的行业选择,更让抗生素研发雪上加霜。与抗癌药“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九个月” 的长期用药周期不同,抗生素的常规疗程仅一到两周,患者用药成本低、药企回款周期短,利润空间远不及抗癌药、慢性病药物。对以盈利为核心目标的药企而言,将资源投入 “低回报、高风险” 的抗生素研发,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于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各大国际药企陆续缩减甚至关停抗生素研发管线,如今全球新型抗生素的研发主力,已从跨国药企转向资源有限的初创公司。
雪上加霜的是,传统研发路径也已走到尽头。自青霉素被发现以来,近 90% 的抗生素都源于土壤微生物的天然产物 —— 科学家通过分离土壤中的放线菌、真菌,从中提取具有抗菌活性的分子。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 “地毯式搜索”,容易分离、活性明确的微生物菌株与分子早已被挖掘殆尽,剩余的潜在资源不仅分离难度极大,还需面对 “活性低、毒性高” 等难题,传统方法的研发效率大幅递减。
一边是新方法“失灵”,一边是老路径 “枯竭”,双重困境之下,抗生素研发陷入了近四十年的“空窗期”。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选择投身其中,这里面有冲动,也有理性。“不想回到前抗生素时代。” 这是杨小教授希望能够把科研成果带动产业的最初动力。
马聪教授提到,他一位长期关注抗菌药研发的同事,在父亲战胜癌症后却反复因细菌感染住院,最终被医生告知“已经没有药可用了,只能回家等待”。杨小教授提到的 27 岁女患者亦如此——年轻、免疫力尚可,但在面对耐药菌时同样败下阵来。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无药可用,只能采取‘等待观察’。”杨小教授在转述意大利临床专家的原话时,语气沉重。她在近期国际会议上获悉,耐药性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引发感染的 28 天死亡率已接近甚至超过 50%。
“这太可怕了,几乎没有其他疾病能在 28 天内夺走一半患者的生命,哪怕是白血病、癌症也做不到。”她这样感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和2024年两次发布的《全球耐药菌重点清单》,耐碳青霉烯的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均被列入“关键(Critical)优先级”,意味着一旦患者感染,医生手中的药物选择极其有限。
马聪教授直言,细菌感染的特点太“极端”—— 要么一周内治愈,要么一周内致死。它不像癌症患者有几年时间四处寻药,像《我不是药神》里那样被众人关注。“细菌感染患者可能三天就没了,连求助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由得感叹。这种“隐匿性”,让耐药菌的威胁始终未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却像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
“为什么能战胜癌症,却输给了细菌感染?” 采访到中段,这句话成为了两位教授和橙果局共同的遗憾。
决定成立公司,两人没有太多纠结。他们将公司命名为元美药业,致力于解决全球抗生素抗药性问题,专注于新型抗菌药物及生物医药先导化合物的研发。
彼时,杨小教授所在的课题组深耕微生物学,对细菌转录机制、耐药靶点有着深刻理解,却在药物设计与筛选环节缺乏突破路径;而马聪教授带着药学与化学合成的背景加入,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我能做药物设计、虚拟筛选,这些对课题组来说是全新的方向。” 马聪教授回忆道。
当两人将微生物学的靶点研究与药物设计的技术结合,很快便有了收获:他们筛选出的首批苗头化合物,不仅展现出明确的抗菌活性,后续的机制研究更验证了设计思路的可行性。
“那一刻特别受鼓舞,感觉这个方向走对了。”杨小教授这样回忆。
真正让两人坚信“是课题选择了我们” 的,是一次意外顺利的实验。当时,他们着手推进一项难度颇高的耐药菌抑制实验,原本做好了反复调试、多次失败的准备,却没想到首次尝试就完全成功。
“我当时拿着结果就往显微镜室跑,马聪教授还在整理数据,看到结果时我们都愣住了。” 杨小教授至今记得那种“被击中” 的感觉,“就像有股力量在推着我们往前走,特别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被眷顾了。”
这份感性层面的“顺”,在理性层面则转化为对新技术的敏锐探索。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药物研发领域涌现出不少颠覆性技术,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很早就意识到,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AI 技术,或许是打破抗生素研发僵局的关键。
“我做冷冻电镜和蛋白结构解析时,就天天和计算机辅助计算打交道,为了处理数据还专门学了 Linux 系统和编程。” 杨小教授对技术的接受度天然很高,她常用的蛋白结构分析软件 Rosetta,后来也逐步引入 AI 功能,这让她更确信新技术的潜力。
早在 2019 年 —— 甚至早于 MIT 那篇 AI 药物开发标志性文章发表前,两人就已启动相关尝试。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首先要说服 AI 领域的合作者认同 “AI 助力抗生素研发” 的可行性,再手把手带着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理解药物开发逻辑、蛋白结构特性与小分子作用机制。
“跨学科沟通太磨人了,早期做出的成果也很初级,根本没法用。” 马聪教授坦言。但他们没有放弃,一点点搭建数据框架、优化算法模型,直到在悉尼的一间民宿里,迎来了突破性的瞬间。
“当时一个学生演示工具,按下按钮的瞬间,屏幕上就跳出了几十个化合物结构 —— 每个看起来都符合成药特性,结构合理性远超我们之前想象的。” 想起那个场景,杨小教授仍难掩激动,“我做了这么多年蛋白计算,以前算一个分子要等很久,结果那天一下子出来这么多优质候选。”
“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震撼的时刻。”她这样形容,正是这个瞬间,让他们更加坚定:AI 不仅是辅助工具,更是能让抗生素研发 “提速” 的关键力量。
而今,他们用自主开发的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发现平台,已成功设计多种具独特靶点、创新结构与全新作用机制的抗菌候选化合物,部分研发项目已进入体内临床前阶段,并取得多国专利保护。


从职业生涯的震撼时刻到基于AI做新药研发,团队规模从2人扩展到20余人
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 —— 他们深知 AI 并非 “万能钥匙”,其价值的发挥离不开数据支撑与人类专家的把控,而突破局限的关键,在于搭建适配抗生素研发需求的专属 AI 平台。
马聪教授从学生时代就与计算机辅助技术结缘,自学 C 语言、考取计算机证书的经历,让他对技术的理解更接地气:“AI 的优势很明确,能基于大数据学习规律,给不同问题提供高概率解决方案,比传统软件灵活得多。” 也正因如此,他们早早为团队引入 AI 人才,希望借助技术加速研发。
但作为初创公司,现实的限制很快显现:“AI 的核心是数据,可高质量的训练集太难拿到了。” 马聪教授无奈地表示,大型药企手握自动化机器人积累的独家数据集,却从不对外开放,“这不仅是我们的困境,也是整个行业的瓶颈,但我们没法强求,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种局限在药物研发的不同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化学合成环节,AI 能发挥切实作用 —— 通过学习海量合成反应的条件与底物信息,针对团队使用的特定起始物料,精准推荐最优反应条件,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可一旦进入临床前与临床阶段,AI 的 “短板” 便暴露无遗。
“为什么很多 AI 生成的分子在临床阶段失败?关键是缺乏足够的体内数据。” 马聪教授解释道,新药审批需要通过毒理、药代等一系列复杂测试,而目前没有足够多的分子 - 体内效果对应数据供 AI 学习,“在需要验证安全性、有效性的环节,AI 能帮的忙最少,还是得靠实验数据说话。”
杨小教授也补充道,业界对“AI 生成结果难验证” 的质疑确实存在,早期研发中他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AI 擅长在特定环境下穷举和迭代,就像下棋时梳理决策树,但它没法像人类专家那样,结合药物机制、蛋白结构特性判断分子的实际价值。” 她始终强调 “AI 辅助” 的定位:“它是工具,不是替代者。”
面对大型药企数据垄断的现实,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团队没有陷入被动,而是以公共数据库为基石,一步步搭建起既贴合抗菌药物研发需求、又具备跨领域拓展能力的专属 AI 平台 —— 他们的思路很清晰:用数据整合破解资源限制,用技术优化实现通用适配。
在抗菌药物研发的核心赛道上,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的数据库成为他们的关键支撑。“EMBL 数据库收录了大量已发表的抗菌相关数据,包括分子结构、抗菌活性等,而且分类很清晰,对我们这种依赖公共数据的初创团队来说,是难得的资源。” 马聪教授解释道。
为了确保数据质量与时效性,团队系统整合了截至 2023 年底的所有相关数据,从最初筛选出的约 7 万个具有抗菌活性的分子中,剔除重复、无效信息,最终保留 3 万多个结构明确、活性数据完整的分子,以此为基础构建了 “抗菌活性预测模型”。这套模型能精准匹配抗菌分子的结构特征与活性表现,为早期化合物筛选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他们并未止步于单一领域的模型开发。考虑到未来可能拓展至其他疾病领域的研发需求,EMBL 数据库在非抗菌领域(如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疾病)的数据分类不完善、抗癌活性数据因实验方法差异难以统一的问题,成为新的挑战。为此,团队将目光转向了 ZINC 数据库 —— 这个包含 600 亿个经生物活性验证分子的 “宝库”,虽覆盖范围广,但活性类型杂乱无章,缺乏明确分类。
“我们的思路是,不纠结于 ZINC 数据库的活性分类,而是通过计算技术提取有生物活性分子的通用结构特征。” 马聪教授介绍道。
团队通过算法优化,从 ZINC 数据库中筛选出具有成药潜力的 “类药性分子”,重点学习其结构与活性的关联规律,再将这套学习成果反向应用于抗菌研究,与基于 EMBL 数据构建的模型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超出预期:在提高 ZINC 数据库采样量、聚焦类药性分子后,新模型的抗菌活性预测效果不仅与专属模型相当,部分指标甚至更优。
杨小教授与马聪教授两位教授先后将事业重心落于香港,这里也是最早向他们抛出橄榄枝的地区。
对于为何选择香港作为科研与事业发展的核心区域,马聪教授从学术平台与学科特色两方面给出了清晰解答。凭借国际化的研究背景,两人曾考察过全球多个地区的机会,而香港理工大学的邀请最终成为关键契机。马聪教授加入该校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后,得以依托校内的“药物研发及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前身为相关重点实验室)开展工作,实验室聚焦药物开发的研究方向,与两人专注的抗生素研发课题高度匹配。
更吸引他们的是该学系的独特设置:不同于多数高校将化学与生物分属不同学系或学院的传统模式,这里实现了生物与化学学科的深度整合,并以药物开发为核心研究目标。这种跨学科融合的学术环境,为两人将早期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拓展,推动从基础科研向实际应用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让初步的科研发现有机会成长为具备临床价值的药物研发方向。
在公司注册地的选择上,马聪教授表示,尽管内地、香港及其他地区均在考虑范围内,但香港对初创企业的政策支持成为重要决策因素。一方面,两人当时已在香港开展工作,且内地大湾区整体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注册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香港创新科技署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计划”、香港科学园的 “IncuBio” 等项目,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了关键支持。
对于从零起步、初期仅拥有技术与初步研究成果的团队而言,直接对接投资人融资难度较大。而香港的这些政府扶持计划,不仅能帮助初创公司快速完成基础搭建,更能提供展示平台,助力团队宣传研发进展,进而吸引到真正能推动公司高速发展的投资机构,为企业初期的生存与成长注入关键动力。
凭借卓越的技术创新和香港的产业影响力,元美药业在成立次年便荣获2019年TechConnect创新奖(Innovation Award)。此后,公司屡获殊荣,包括在第48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摘得铜牌、入选2023年Falling Walls年度科学突破(科学新创/Falling Walls Venture类别)、跻身2023年勃林格殷格翰创新奖前五强,并成功晋级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决赛。

元美药业获得2019 TechConnet 创新奖(Innovation Award),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元美药业入选2023年 Falling Walls 年度科学突破(科学新创 / Falling Walls Venture 类别)


杨小教授在2023年 Falling Walls进行分享
元美药业获得第48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铜奖


2024 BIO SanDiego
与此同时,香港的地理位置优势将助力公司的国际化布局。团队计划依托大湾区,拓展美国、欧洲等国际市场,在这些地区推进临床前开发工作,并尝试“中美双报”,争取获得在中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地区开展临床试验的资格。
他们强调,抗生素需求具有全球性,并非局限于中国市场,国际化布局不仅能为公司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能通过海外市场的收益反哺国内研发,形成“全球研发 - 全球市场” 的良性循环。
专家点评:

尚骏投资总经理陈奕群
元美这个项目是具备投资价值的。瞄准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危机,切入近40年无新类别抗生素问世的巨大市场空白,这一点我们从很多临床专家那边也得到了反馈与佐证。另外他们团队来自高校多学科交叉,由微生物学与药物化学等顶尖学者组成,技术路径明确,已构建自主AI药物设计平台,并在早期筛选中验证了其可行性。
项目起点于香港,具备国际化布局与政策支持优势,同时大湾区也有非常丰富的医疗资源,能够响应这一项目的落地。尽管抗生素研发存在商业化挑战,但其战略意义与社会价值突出,有可能可以打造成中国原研、全球解决的标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