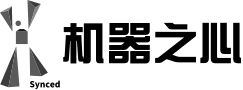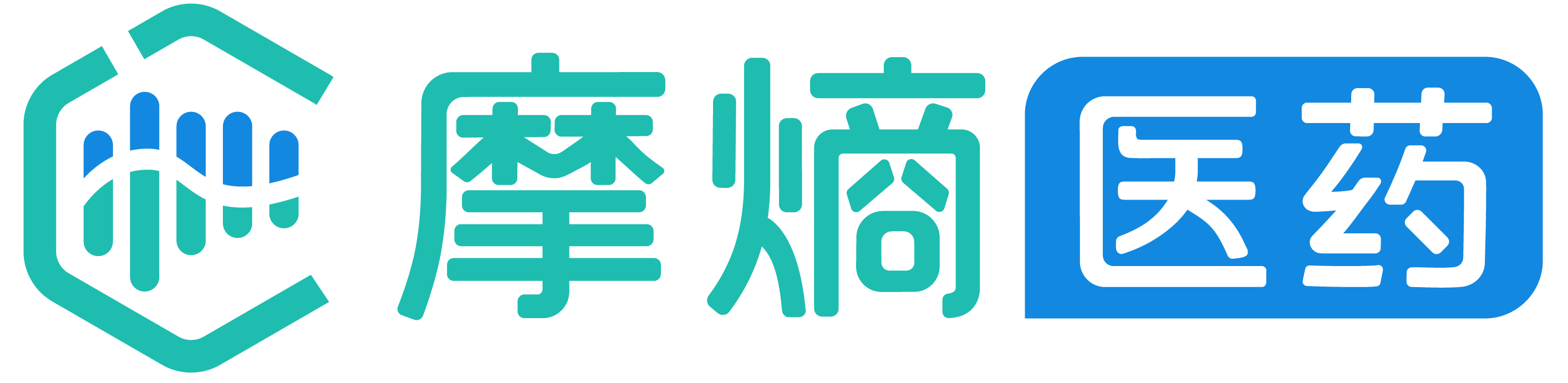在地球上,一场持续了数十亿年的战争从未停歇。它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微观世界——海洋深处、土壤之中、甚至我们的身体里,交战的双方是数量约10的38次方的细菌和数量更为庞大的病毒军团(噬菌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真实上演在地球每个角落的生存竞赛。
在这场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细菌进化出了各种令人惊叹的防御武器。它们会切割病毒的组件,剥夺病毒复制所需的关键成分,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附近的同伴。而病毒也在不断进化出反制措施,形成了一个持续升级的攻防循环。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塑造了地球上最古老、最复杂的免疫系统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微生物学家刚刚开始理解这场古老战争的全貌,但微生物的免疫机制已经催生出了革命性的生物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开启分子生物学时代的限制性内切酶,到21世纪初期改变整个生物学研究范式的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改变世界的工具都源自细菌的防御系统。
而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这个巨大的工具库中寻找下一个能够引发技术革命的发现。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进化生物学家Eugene Koonin对此发出断言:“我敢说,细菌和古菌使用一切你能想象到的方法进行防御——还有一些你无法想象的。”
其实不止今天大家熟知的CRISPR技术,微生物免疫机制对人类生物技术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科学家发现细菌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蛋白质——限制性内切酶,它可以在特定位点切割DNA。这种蛋白质原本是细菌用来切碎入侵病毒DNA的武器,却意外地成为了人类开启分子生物学时代的钥匙。
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它,科学家终于能够精确地切割和拼接DNA片段,这使得创造转基因生物、DNA指纹鉴定、基因克隆和重组DNA技术成为可能,奠定了现代基因工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让科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细菌在与病毒的斗争中进化出的防御系统,可能蕴藏着更多改变世界的技术秘密。
CRISPR的发现故事则始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观察。1987年,日本科学家在大肠杆菌基因组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重复序列,但当时没有人理解它们的意义。直到后来科学家才意识到这些序列间隔区的DNA片段来自噬菌体,也就是说细菌似乎在记录曾经攻击过自己的病毒信息,就像建立了一本通缉犯档案。2007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Rodolphe Barrangou和丹麦食品公司Danisco的科学家Philippe Horvath通过实验证实,CRISPR确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细菌用它来识别和摧毁特定病毒的基因组。
真正的技术突破发生在201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证明CRISPR-Cas9系统可以被编程来切割任何指定的DNA序列。这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精确删除特定基因、修正致病突变、插入新的基因功能。
相比传统的基因编辑方法,CRISPR更简单、更便宜、更精确,这一发现的影响是爆炸性的。它不仅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更在2020年为两位发现者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毫不夸张地说,CRISPR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生物学研究的方式。它开启了治疗遗传疾病的新途径,使农作物改良有了新工具,甚至让消灭疾病媒介成为可能。首个CRISPR疗法已经获批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这标志着基因编辑正式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但这仅仅是开始,科学家们相信,CRISPR所代表的只是微生物防御系统这座宝库的冰山一角。
简单来说,CRISPR-Cas系统就像一把配备了GPS导航的分子剪刀。首先,引导RNA携带着目标序列的信息,就像一张通缉令;然后,Cas蛋白在引导RNA的带领下扫描整个基因组,寻找匹配的序列;一旦找到目标,Cas蛋白就像剪刀一样切断DNA双链;最后,细胞自身的DNA修复机制启动,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插入新的基因序列或删除有害片段。
这个看似简单优雅的系统,需要一个额外的识别序列作为辅助,科学家称之为PAM序列。这个短小的DNA片段帮助Cas蛋白准确定位和结合目标DNA,确保不会误伤其他相似的序列。正是这种精密的识别机制,使得CRISPR能够在庞大的基因组中找到正确的编辑位点。
在实际应用中,CRISPR已经在多个领域展现出巨大价值。
在医学治疗方面,除了已获批的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疗法,研究人员正在开发针对癌症的免疫疗法,通过编辑免疫细胞使其更有效地攻击肿瘤,同时也在探索针对HIV等病毒感染的基因治疗方案。
在农业领域,科学家利用CRISPR培育抗病作物,提高作物的营养价值,使其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环境。
在基础研究层面,CRISPR加速了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帮助科学家快速理解基因功能,创建更准确的疾病动物模型,深入研究基因在进化中的作用。
然而,CRISPR并非完美无缺。脱靶效应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Cas蛋白有时会切割到与目标序列相似但并非目标的位置,这可能导致意外的基因改变。
递送困难也是一大挑战,如何将CRISPR系统有效地送达体内的目标细胞,特别是难以触及的器官和组织,仍然是制约其临床应用的瓶颈。PAM序列的限制意味着不是所有想要编辑的位点都能被Cas9识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的灵活性。
此外,关于人类胚胎编辑的伦理争议也从未平息,治疗性编辑与增强性编辑的边界在哪里,生殖细胞编辑是否应该被允许,这些问题困扰着科学界和社会。
正是这些局限性和挑战,促使科学家们继续在微生物的防御系统中寻找新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2011年,Eugene Koonin和Kira Makarova及其同事发现细菌和古菌基因组中的免疫基因倾向于聚集形成“防御岛”。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用已知的防御基因作为路标,在其附近搜索新的防御机制。这一发现就像找到了藏宝图的关键线索,使新防御系统的发现速度大大加快,为寻找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奠定了基础。
在防御岛研究方法的推动下,结果是惊人的。近年来,研究人员报告了数百个潜在的防御基因。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Rotem Sorek表示,他们的研究团队每周需要讨论五篇新论文,却仍然无法涵盖所有内容。莫斯科分子与细胞生物学中心的Artem Isaev也感叹,新发现的速度如此之快,研究人员甚至来不及讨论所有的进展。
这种研究热潮背后,是科学家们对发现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的期待。
令人震惊的是,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许多细菌防御系统与人类和植物的免疫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哈佛医学院的Philip Kranzusch在研究人类免疫蛋白cGAS时,偶然发现细菌也拥有结构极为相似的系统——CBASS。这两个系统不仅结构相似,工作方式也几乎一致:它们都能检测外来DNA,产生相同的信号分子,使用相同的受体蛋白STING,最终触发细胞死亡来阻止感染扩散。类似的发现接踵而至,科学家发现了细菌版本的gasdermin蛋白、原核生物版本的viperin蛋白等,这些蛋白在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中采用相似的防御策略。
来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Aude Bernheim指出:“从进化角度看,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科学家原本认为,面对持续的病毒攻击,免疫系统应该快速进化,导致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的防御机制出现巨大差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共同祖先中进化出的防御系统,经过数十亿年仍然保持下来,创造出跨越生命形式的平行生物学机制。
正是基于这些发现,一系列有潜力挑战或补充CRISPR的新工具正在涌现。这些工具各有特色,在不同场景下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首先是Argonaute系统,这是一种最初在真核生物中发现的免疫反应,如今在微生物中也找到了对应版本。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Daan Swarts深入研究了这个系统,发现它具有几个显著优势。首先,与CRISPR不同,Argonaute系统不需要PAM序列,这使它比CRISPR更灵活,可以靶向更多的基因组位置;其次,它所需的引导序列更短,这不仅降低了制造成本,也使得整个系统更容易生产和应用。Swarts团队开发的基于SPARTA系统的诊断测试,可以通过颜色变化或荧光来检测任何目标序列。Swarts自信地表示:“基本上,任何类型的序列都可以用这些Argonaute系统检测到,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限制。”从商业角度看,Argonaute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在CRISPR专利已经饱和的情况下,Argonaute领域更容易获得新的专利保护。
其次是TIGR-Tas系统,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张锋教授发现的类CRISPR系统。TIGR-Tas的全称是串联间隔引导RNA-TIGR相关蛋白,它像CRISPR一样采用双组分设计来检测特定DNA序列,但同样不需要PAM序列的限制,可以实现更自由的编程切割。更重要的是,TIGR-Tas的组件比CRISPR更紧凑,体积更小。这一特点在基因治疗中特别有价值,因为目前基因治疗的一个主要限制是递送系统能携带的分子货物量有限。腺相关病毒载体作为主要的递送工具,其装载能力是固定的,更小的编辑系统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递送到组织中,为突破递送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
再次是Retron系统,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的遗传元件,直到2020年才确认其免疫功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格拉德斯通研究所的Seth Shipman看到了retron在基因编辑中的独特价值。Retron使用逆转录酶从RNA模板创建DNA,可以在细胞内部大量生产单链DNA拷贝。它采用精巧的毒素-抗毒素机制:RNA模板连接的单链DNA产物折叠成双螺旋,形成一个笼子束缚着毒素。如果噬菌体酶试图修改这个DNA结构,就会引起结构变化释放毒素,从而消灭被感染的细胞。对于CRISPR基因编辑来说,递送大量DNA模板一直是个挑战,而使用retron系统,科学家可以让细胞自己在内部批量生产模板拷贝。Shipman已经用这种方法成功编辑了细菌、酵母、人类细胞和噬菌体,并联合创办了一家公司推进技术开发。
除了这些编辑工具,病毒的反击武器也带来了新的应用思路。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Joseph Bondy-Denomy在2011年还是研究生时,就发现了Anti-CRISPR蛋白——一种能够关闭细菌CRISPR防御系统的噬菌体武器。现在已知有100多个Anti-CRISPR蛋白家族,它们通过不同机制工作:有的粘附到Cas蛋白上阻止其结合或切割DNA,有的修饰或切割引导RNA,还有的干扰CRISPR复合物的组装。这些关闭开关为精细调控基因编辑提供了新手段。由于Cas酶经常不仅切割目标位点,还会切割相似的脱靶位点,而靶向编辑最快、最有效,使用弱化的Anti-CRISPR或延迟其活性,科学家可以在预期的编辑完成后及时停止Cas酶的活性,从而防止大部分不良的脱靶编辑。Bondy-Denomy的初创公司Acrigen Biosciences正在开发这种方法用于基因治疗,以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精确性。
这些新工具的医疗应用潜力尤其令人兴奋。
许多细菌防御机制采取自我破坏的策略,通过阻断自己的基本过程来挫败病毒入侵者,所以这些机制可能成为新型抗生素的来源。Bondy-Denomy形容这是抗菌酶的金矿。CBASS系统、gasdermin蛋白、retron系统以及其他毒素-抗毒素系统,都可能被改造成抗菌武器。挑战在于这些系统都是在细胞内进化而来的,因此需要找到方法将它们递送到细菌内部,或者激活细菌中已经存在但尚未启动的防御系统。
北卡罗来纳州莫里斯维尔的Locus Biosciences公司就采用了一个巧妙的策略:他们设计了携带抗菌CRISPR系统的噬菌体,这个CRISPR系统不针对病毒,而是导致细菌摧毁自己的关键基因。在女性尿路感染的小型临床试验中,这种疗法成功降低了病原体水平并消除了症状,展示了将微生物防御系统转化为治疗手段的可行性。
噬菌体治疗本身也将从这些研究中受益。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Asma Hatoum-Aslan提醒说:“一旦我们开始噬菌体治疗,我们将面临噬菌体耐药性问题。关键是提前了解并将一些干预措施纳入我们的噬菌体治疗中。”对微生物防御系统的深入理解,将帮助科学家预测和预防细菌产生耐药性,设计更有效的噬菌体疗法,开发组合治疗策略,从而让这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在抗生素耐药性日益严重的今天重新焕发生机。
那些与人类免疫系统平行的细菌防御系统,更是指向了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癌症或感染的新途径。原核生物viperin产生的转录阻断分子可能被转化为抗病毒药物。Kranzusch推测,CBASS系统产生的信号分子可以被改造成疫苗佐剂,增强身体对疫苗的反应。而Bondy-Denomy和合作者去年发表的研究显示,使用Anti-CBASS蛋白可以在人类细胞中沉默cGAS-STING系统,这可能产生抗炎效果,为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开辟新路径。Bernheim和其他微生物学家正在与人类免疫学家建立合作关系,探索这些跨越生命形式的免疫机制如何能够相互启发,为人类健康服务。
推动这个领域加速发展的,还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今年发表的预印本研究显示,Bernheim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Michael Laub团队都在使用机器学习识别新的防御系统候选者。机器学习可以分析海量的基因组数据,预测蛋白质结构,识别新的防御岛,大大加速候选系统的筛选过程。Laub的评估令人振奋:“还有数千个新系统有待发现。”这意味着我们目前看到的,可能只是微生物防御系统这座宝库的很小一部分。
CRISPR已经证明,微生物防御系统可以成为强大的生物技术工具。现在,科学家正在构建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工具箱,每种工具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适用场景。
首先,CRISPR-Cas作为成熟的技术,继续在精确基因编辑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Argonaute系统因其无PAM限制的特性,提供了更灵活的应用可能;TIGR-Tas的紧凑尺寸使其特别适合基因治疗递送;Retron系统通过内部DNA合成增强了编辑效率;Anti-CRISPR则为精细调控和提高安全性提供了新手段。正如Koonin所说:“要比CRISPR做得更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这些系统中的一些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这个领域的发展路径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从基础发现到临床应用,需要经历识别新防御系统、理解工作原理、改造成实验室和临床工具、优化效率和安全性,最后通过监管批准推向临床应用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学科的协作,这也是为什么未来的突破将越来越依赖多学科融合。
计算生物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基因组数据挖掘,科学家可以从海量的微生物基因组中识别新的防御系统。蛋白质结构预测技术,特别是AlphaFold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使得理解这些防御系统的分子机制变得更加容易。系统进化分析则帮助研究人员追溯这些防御机制的起源和演化历程,理解为什么某些机制能够跨越数十亿年仍然保持下来。
合成生物学为这些天然防御系统的改造和优化提供了工具。科学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使用自然界中发现的系统,而是开始设计新的防御机制,优化现有工具的性能,甚至创造混合系统来结合不同工具的优点。这种理性设计的思路,正在加速从发现到应用的转化过程。
临床医学的需求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个性化基因治疗需要更精确、更安全的编辑工具。精准诊断工具的开发需要能够快速、特异性检测目标序列的技术。新型抗菌策略的探索需要理解细菌如何防御病毒攻击,以及如何将这些机制转化为对抗病原菌的武器。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强大技术带来的伦理和社会挑战。基因编辑能力的提升,使得治疗性编辑与增强性编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生殖细胞编辑的规范制定,需要在科学可能性和社会伦理之间找到平衡。改造微生物释放到环境中的安全性评估,需要考虑长期的生态影响。技术的可及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何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公平获取这些先进疗法,如何控制成本使其具有可负担性,如何促进技术转移而不是加剧全球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获得强大技术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培养相应的责任感和前瞻性思考能力。
细菌和病毒之间数十亿年的战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似乎取之不尽的创新源泉。从限制酶到CRISPR,再到现在正在涌现的众多新系统,每一次发现都在推动生物技术的边界。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令人目不暇接,新发现的速度之快,甚至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难以跟上节奏。
虽然没有单一技术看起来能够完全取代CRISPR成为本世纪最具变革性的生物学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探索的终结。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拥有多样化工具箱的时代,每种工具都在特定场景下发挥独特价值。
这些发现也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大自然已经用数十亿年的时间进行了最精妙的工程设计。我们的任务不是从零开始创新,而是学会阅读和理解大自然这本巨大的工程手册。
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下一个CRISPR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我们如何从大自然最古老的斗争中,找到解决人类最现代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同时,借用其智慧服务于人类福祉?我们如何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保持对伦理边界的敬畏?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由这一代和下一代科学家共同书写。而这个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智慧最激动人心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