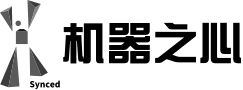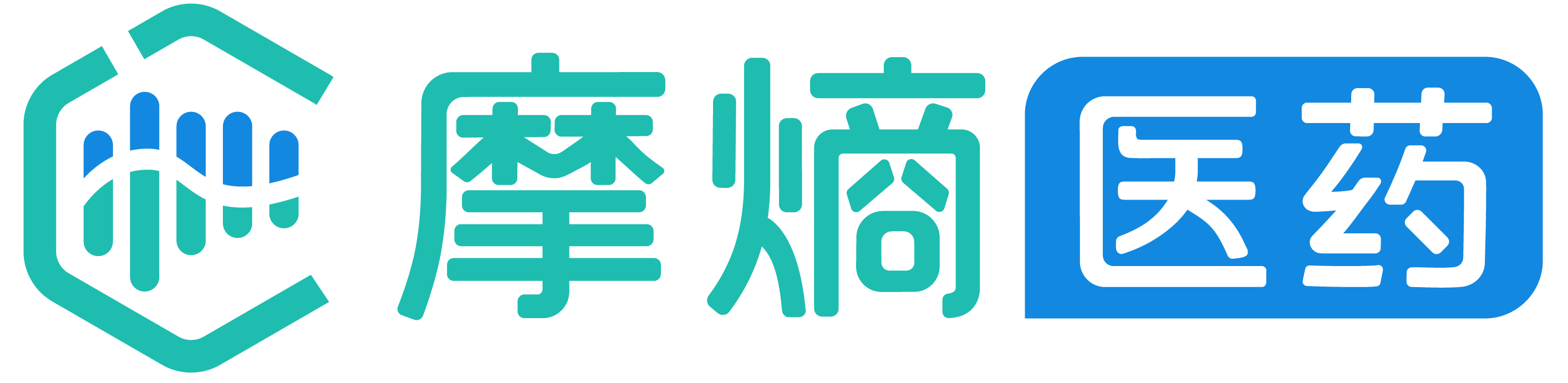2008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撼动了中国汶川。
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画面:废墟下被压断双腿的孩子,失去右臂的中学教师,被钢筋贯穿骨盆的老人……每一个镜头都是一个骨科创伤的案例,每一声呼救都牵动着王金武的心。
作为当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一名骨科医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导及博士后导师),王金武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医疗队。在那里,有无数断肢需要再植,无数骨折需要固定,无数伤痛等待救援——这是每一个骨科医生最本能的战场。
"我是学骨科的,这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前线!"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转了一个弯。由于灾区外伤救治力量的统筹调整,不再急需第一批报名的骨科医生大规模进驻。王金武的名字被调整到了另一个名单上:出国进修。
心里装着汶川,人却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航班。
几个月后,他出现在了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
这里是全球顶尖的医疗圣地,平静,有序,与满目疮痍的汶川似乎是两个世界。但在王金武的内心,一场无声的"余震"正在发生。
在跟随前美国肩关节外科学会主席(Joseph Iannotti)教授学习的日子里,每当他走进手术室,看到那些精密的手术器械、先进的内固定系统、微创的关节镜设备,脑海里总会闪回那些汶川的画面。
"如果地震救援现场有这些设备,该有多少生命能被挽救?该有多少人可以避免残疾?"
这个念头像钉子一样扎在心里,挥之不去。
他开始留意这些医疗器械的品牌——几乎清一色都是美国、德国、瑞士的公司。再想想国内医院的手术室,那些昂贵的进口设备,代理商层层加价后高得离谱的价格,以及关键时刻"卡脖子"的技术垄断。
"为什么我们中国自己造不出来?"
带着这个疑问,他开始观察这所医院独特的景象:走廊墙壁上,挂的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一排排"光荣榜"。榜单上是医生和工程师的合影,他们并肩微笑,手捧着共同研发的新型医疗器械。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项改变临床治疗的技术创新。
医生和工程师,在这里不是两个世界的人,而是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的战友。
"为什么他们能研发出来?国内为什么研发比较少?"
他开始疯狂地寻找答案。观察、询问、对比,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国外是先学工,然后再学医,他们医工结合的基础非常好。而国内,我们医生的培养都是学临床医学,但是工科没有基础。"
在当时的中国,医生和工程师分布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医生不懂材料力学,工程师不懂解剖病理。中间这道看不见的鸿沟,阻断了中国医疗器械自主研发的道路。
更让人惋惜的是,即便有好的创意和设计,也很难转化成真正的产品。实验室的样机只能"喂老鼠",拿不到注册证,上不了临床,救不了病人。大量的科研经费最终变成了束之高阁的论文,却没能变成摆在手术台上、能真正用来救人的"武器"。
站在克利夫兰的走廊里,王金武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画面:
如果有一天,中国医生手中拿着的,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先进设备,那该多好。
他意识到,自己虽然错过了一个救死扶伤的战术战场,却意外撞进了一个更宏大、也更艰难的战略战场——医工结合。
在前线,他一次只能救几十个、几百个病人。
但如果能打通医疗器械自主研发的道路,他可以让成千上万的医生,拥有更好的"武器",去救治成千上万的病人。
"如果我们只做开刀匠,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医工结合,是我们国内医疗企业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
这个念头,在2008年异国他乡的深夜里扎下了根。它不仅改变了王金武一个人的职业轨迹,也将在未来的16年里,深度参与中国医疗器械转化制度的一场破冰之旅。
如果人生是一场精密的实验,那么王金武进入医学领域,最初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系统误差"。
1989年的夏天,山东高考结束。高中毕业生王金武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写下了一连串当时最时髦的专业:"工商管理"、"经济学"、"商业"。在那个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的年代,"下海"是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
"当时高考,实际上也没有特意去选医学,"多年后,坐在上海交大转化医学大楼的办公室里,王金武回忆起这段往事,语气中带着几分对命运安排的感慨。
命运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调剂"到了滨州医学院。
初入医学院,面对枯燥的解剖图谱和晦涩的病理名词,这个原本志在商海的年轻人感到了一阵迷茫。他在寻找一个理由,一个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理由。
转折发生在大二那年。
当时王金武的的爷爷生病住院,他请假回去陪护。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那些平日里只停留在课本上的药理知识、护理常识,突然变成了手里实实在在的"武器"。
"爷爷,这个药是治这个的,虽然苦但是管用..."
"这样躺着虽然不舒服,但是对恢复好..."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用学到的知识给老人解释病情,提供专业的建议。原本因为未知而焦虑不安的老人,在孩子的安抚下,眼神逐渐变得安详和信任。
"还没有毕业就能学以致用,体验到不一般的职业成就感。尤其是大家比较信任我,这段经历破开了我专业选择上的迷雾。"
这种信任,像一道光,照亮了他原本有些灰暗的学医之路。他开始隐约感觉到,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建立在技术之上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托付。
其实,关于"医疗的温度",早在更久远的童年,就已经在他的记忆里埋下了伏笔。
小时候因为贪玩,王金武的胳膊肘关节脱位,剧烈的疼痛让孩子哇哇大哭。父母心急如焚,带着他找到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在王金武的记忆里,那位赤脚医生没有穿白大褂,手上有常年劳作留下的老茧,但动作却出奇地轻柔。他一边笑着逗孩子说话分散注意力,一边轻轻地摸索着关节的位置。
"咔哒"一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脱出的骨头已经复位了。疼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奇的轻松感。
"那种感觉非常深刻,"王金武回忆道,"而且也非常便宜,几乎没要钱。家长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小孩子也没有因为开刀受很多罪。"
简单、有效、便宜、有温度。
这位不知名的赤脚医生,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年幼的王金武上了一堂关于"好医生"的启蒙课。这颗种子,在多年后他面临复杂的医疗技术选择时,依然顽强地指引着方向:能不能更微创?能不能更便宜?能不能让病人少受罪?
带着这份初心,王金武在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深。
从滨州医学院毕业后,他考入了解放军第89医院全军创伤骨科中心攻读硕士,随后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攻读博士,师从我国手外科奠基人、著名的顾玉东院士。
90年代的中国,显微外科和断肢再植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在手术室里,王金武见证了更多技术带来的"奇迹"。
那些因为工伤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因为车祸断裂的肢体,在显微镜下,通过医生那一双双精细的手,血管被一针针缝合,神经被一丝丝对接。
"苍白的指尖慢慢红润起来,冰冷的肢体重新有了温度。"
这种"起死回生"的视觉冲击,让年轻的王金武深受震撼。"通过自己的操作,把断肢接上还能活...感觉医生这个技术非常精细,非常伟大。"
从赤脚医生的手法复位,到院士级别的显微再植,王金武逐渐确信,不仅仅是他选择了医学,更是医学选中了他。
他要在修复人体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他没想到的是,多年后,他要修复的,不仅仅是病人的断肢,还有中国医疗器械转化制度中那个巨大的"断层"。
2009年7月,王金武做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有些"傻"的决定:放弃了在美国继续做Fellow的机会,也没留在待遇优渥的海外医疗机构,而是选择回国。
召唤他回来的,是对"医工结合"的执念,也是一位长者的感召。
在美国期间,王金武应约参加了一次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康复医学与工程大会(CRME)美国重要嘉宾邀请。这是一场全球顶尖的学术盛会,而担任大会主席的,正是来自中国的一位院士——戴尅戎。
戴尅戎,中国工程院院士,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也是中国"医工结合"的拓荒者。早年间,当大多数骨科医生还只盯着手术刀时,戴院士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工程学的原理应用到骨科治疗中。
"你是戴院士的学生吗?"在国外邀请医学与康复领域国际著名专家时,王金武被多次问到这个问题。虽然当时他还不是,但那份对数字医学、3D打印、康复工程的共同狂热,让两代医生的心跳到了同一个频率上。
回国后,王金武通过"浦江人才计划"引进,正式加入了上海九院骨科,成为了戴尅戎院士团队的一员,并在之后成为了他的博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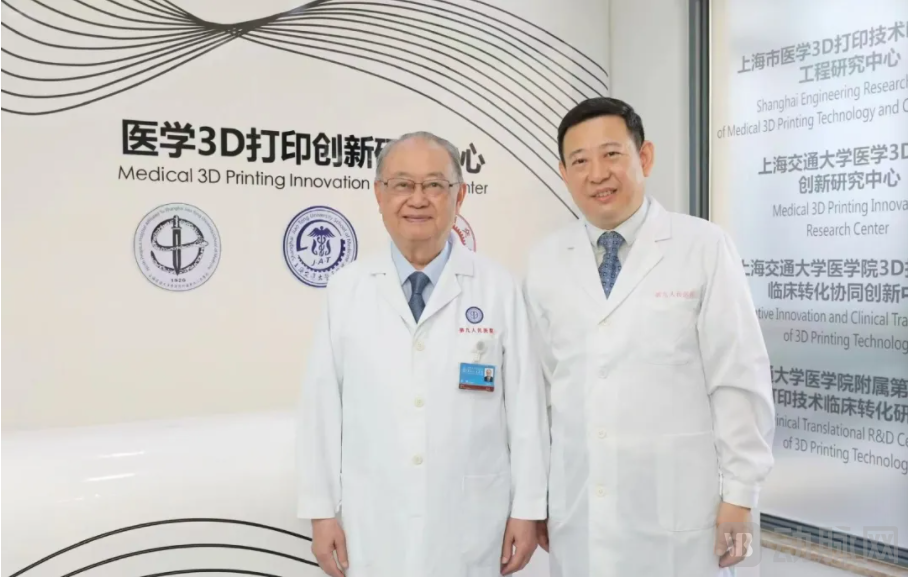
图:戴尅戎院士与王金武教授(受访者供图)
"我是站在高原上建高峰。"王金武这样形容这段师承关系。戴院士已经铺垫了厚实的地基,而他要做的,是在这之上盖出新的高楼。
万事开头难。虽然"医工结合"的理念在克利夫兰听起来很美,但在当时的中国落地,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医生和工程师的语言体系完全不同,常常是"鸡同鸭讲"。
"医工结合要早期就要给工程师交流,"王金武深有体会,"而不是说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交给工程师,工程师做完了以后拿来你一看,哎,你说不行重新返工,时间也浪费了。"
为了打破这层隔膜,王金武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翻译官——3D打印。
"你看一个片子(X光片),工程师有的时候看不清楚。但我把它(骨骼模型)打印出来,工程师也能看懂,医生也能看懂。"
借助3D打印的实物模型,医生的临床需求与工程师的技术语言实现了直觉化的对接:哪里需要切除,哪里需要支撑,在模型上一目了然。这种可视化的交流,让原本语境迥异的两个领域,真正达成了深度的共识。
他们瞄准的第一个"敌人",是困扰无数老年人的骨关节炎。
在传统治疗中,骨关节炎到了晚期往往只能换关节。但在早中期,病人依然很痛,却无药可救。王金武团队发现,很多疼痛是因为膝关节受力不平衡造成的——内侧髁受力太大,磨损严重。
"既然基因因素改不了,炎症因素要靠药,那力学因素我们能不能解决?"
利用上海交大在机械工程方面的深厚底蕴,王金武团队设计了一款个性化的3D打印膝关节矫形器。
"内侧痛,我们通过矫形器,把内侧的力量转移一部分到外侧。力学平衡了,这样器官就不痛了。"
这个听起来简单的原理,实行起来却需要极高的精度。但这一次,医生懂了力学,工程师懂了临床。当第一位患者穿戴上这个量身定制的矫形器,惊讶地发现走路不再钻心地疼时,王金武知道,路走通了。
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宽,在戴院士的支持下,王金武教授开始筹建"上海康复辅具与老年福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这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一个生态。从最初的几家单位,发展到如今拥有206家理事单位,其中三分之一是高校和医院,三分之二是企业。医生出需求,高校出方案,企业出产品。
在这个平台上,医生不再是孤独的修补匠,而是成为了整个医疗创新产业链的指挥官。
在王金武教授回国探索医工结合的那几年,中国生物医药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变局。
2013年,一项国家级战略正式立项——"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这是中国继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中心之后,在生物医药领域布局的又一个"大国重器",也是中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转化医学大科学设施。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该项目的法人单位,承担起了一个沉甸甸的使命:打破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壁垒,解决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问题。
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与王金武个人的职业困境,在"死亡之谷"前相遇了。
在科研界,"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是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词。它指的是从实验室的样机,到临床上真正能用的产品,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里,填满了注册证、生产许可证、质量体系考核、临床试验、医保代码等无数复杂的关卡。
多年前,有位领导在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时,曾感慨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不少高校科研院所曾经拿了很多国家的经费,但由于存在科研转化死亡之谷的困境,不少成果倒到下水道里去了,喂了老鼠了。"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在场的科研人员。话虽然重,却道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大量的科研经费变成了纸面上的论文,却没能变成产品造福百姓。
"如果我们拿到注册证以后,就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省去无数繁琐的程序,真正实现我们医生和医学研究的初衷——造福伤残,造福社会。"王金武暗下决心,绝不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喂老鼠"。
但是,这条路太难了。
在过去,高校和医院是不允许直接持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这意味着,医生发明的技术,必须先卖给企业,由企业去申请注册。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的纠纷、利益的分配、技术的走样,无数个坑等着科研人员去跳。
直到"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MAH)的试点推行,一道曙光出现了。这个制度允许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直接申请注册证,委托企业生产。这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不谋而合。
王金武教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
2019年,一张意义非凡的证书颁发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手中——这是国内首张由高校和医院通过注册人制度获得的3D打印医疗器械注册证。
这张薄薄的纸,重如千钧。它意味着,中国的高校和医生,终于可以直接打通从实验室到病床的"最后一公里"。这也标志着,依托于转化医学国家重大设施的"先行先试"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不能光给戴院士团队自己拿注册证,"当时的交大校长对王金武说,"既然路走通了,还要帮其他人走。"
于是,"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研究与临床转化服务中心"应运而生。戴尅戎院士任名誉主任,王金武任执行主任。
这就好比在"死亡之谷"上架起了一座桥。
在这个中心里,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对接医疗器械监管部门,有专门的工程师负责样机定型,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临床试验设计。年轻的医生和教授们,再也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审批流程中乱撞。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2025年,王金武团队帮助交大各个课题组拿到了30多个医疗器械注册证。而到2026年,这个数字预计将突破50个。
这些注册证背后,是几十个可能被"埋没"的创新技术,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走向市场,走进医院,用在病人身上。从3D打印内植物到康复机器人,每一个成果的落地,都是对当年那句"喂老鼠"批评的最好回应。
除此之外,为了让转化不仅停留在纸面,更落实在产业上,王金武还推动建立了长三角(常熟)转化基地和山东日照转化基地,在上海宝山建立了GMP标准的生物3D打印医疗器械生产车间。
"不再是写完论文就结束了,"王金武说,"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从专利到注册证,从生产许可证到医保代码,每一步都走通,这才是真正的转化。"
拿到了注册证,打通了转化路,王金武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从"制造"到"再造"。
3D打印技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打"模型",用来做手术规划;第二阶段是打"内植物",比如钛合金关节,用来替换病变的骨头。但这依然是"死"的材料,无法跟随人体生长,也无法降解。
"我们能不能打印一个跟人体一样的、能生长的、活的器官?"
这就是第三阶段:生物3D打印。而在这个领域里,王金武团队正在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生物3D打印机器人。
在上海九院的实验室里,这台看起来充满科幻感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一项精细的操作。它不仅是在"打印",更像是在"种地"。它使用的"墨水"不是塑料或金属,而是包含着活体细胞、生长因子的生物材料。
"皇冠上的明珠就是可以打软骨,打完了以后把这个关节软骨给修复。"王金武介绍道。
这就是他一直倡导的"保膝保髋"理念。
"就跟那个牙齿一样,牙齿有个洞,补一补,对吧?"王金武打了一个极通俗的比方,"我们关节有个小洞,就把它换关节,实际上不合算的。"
这台机器人,就像是一个微型的"关节维修师"。它可以在微创的情况下,通过关节镜通路进入人体,在缺损的软骨部位,原位打印出新的软骨支架和细胞。这些细胞会慢慢长成新的软骨,而支架则会慢慢降解消失。最终,病人得到的是一个完好如初的、自己的活关节。
这种技术一旦成熟,将彻底改变骨关节炎的治疗版图。
从"换"到"修",背后是王金武团队多年来在9种生物墨水、2套打印机软硬件上的技术积累,也是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牵头的3个科技部重点专项的结晶。
但王金武的愿景不止于此,不仅要"治",还要"防"和"康"。
在山东青州,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正在进行,王金武团队利用数字化筛查技术,对当地11万名儿童进行了足畸形和脊柱侧弯的筛查。
"脊柱侧弯如果到了要开刀的地步,手术费起码要十几万,"王金武深知大手术对家庭的重压,"而现在的早期介入是无创的,不需要动刀。如果因为错过时机导致孩子残疾,那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才是巨大的。"
通过早期筛查发现问题,通过3D打印矫形器进行无创矫正,再通过生物打印修复损伤,最后配合云康复平台进行术后训练。
从早期预防,到中期干细胞、生物打印治疗,再到后期关节置换,正如王金武所说:"我们对于骨关节炎,从早期、中期到后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16年前,在克利夫兰,王金武是一个望着满墙发明感叹"为什么我们没有"的中国留学生。
16年后,在上海,他已是国际生物3D打印标准的制定者。
这份成就的分量,可以用一串闪光的数据来衡量:
作为"十三五"和"十四五"两期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王金武团队完成了9种生物墨水的研制,开发了2套3D生物打印机软硬件产品,发表包括Nature与Science旗下子刊在内的高质量论文100余篇。2021年,他们的生物3D打印项目成果被《Nature》官网专题报道;2024年,他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更重要的是,他们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生物3D打印标准和首个3D打印康复辅具标准,总共制定了14项医疗器械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在国内使用,还成为国际参考。
这不仅是个人身份的逆袭,更是中国在这一领域从"跟跑"到"领跑"的缩影。
"在3D打印方面,国内的金属3D打印标准比美国晚了三个月,"王金武坦言,"毕竟是起步阶段,我们还在努力追赶。"
"但是生物3D打印和康复具3D打印的标准都是我与戴院士牵头的,我们也比美国要早。"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中透着自信。
如今,在3D打印医疗器械领域,欧盟、美国的一些单位甚至会主动向中国药监局寻求一些标准文件作为参考。中国制定的标准,开始成为世界的尺子。
在访谈进行的当天,王金武刚刚接待了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市长代表团。
这些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朋友,对中国先进的数字医学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王金武团队研发的康复设备、3D打印技术,正准备通过合作走出国门,出口到这些国家。
"原来我们是与国外跟跑、并跑,要实现超跑,只有中国自己科研人员掌握核心技术,再通过转化形成自己的产品。"
这位曾经默默无闻、出国深造的年轻医生,经过半生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他在2021年接受《Nature》杂志专访时,这样阐述自己的研究使命:
"生物3D打印在创造具有生理结构功能并能自我修复的组织器官方面,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富有临床转化前景的工具。然而目前也存在很大的挑战:除了高精度打印的要求外,还需制备优良特性的生物墨水以及构建生物活性微环境。"
这段话道出了他的清醒:技术的突破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实验室的成果走向临床,造福病人。
面对成绩,王金武依然保持着那份科学家的清醒与诚实。
当被问及生物打印的未来挑战时,他没有回避困难:"你好比我们现在通过生物打印一个肝脏,它现在还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解毒功能,打印一个肾脏,也还没有办法排出尿来……但看着形象。"
他坦言,打印复杂的器官,在材料、细胞、因子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不吹嘘、不浮夸的态度,恰恰是对科学最大的敬畏。
“尽管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技术进步,但想要解决临床治病的需求,还有很远的路需要走。”
如果你在上海九院或者交大闵行校区看到一个步履匆匆的身影,那你可能刚好与王金武教授擦肩而过。医学这个与时间和死神赛跑的行业早让他习惯了通过快步行走来“抢时间”。
"我平常在医院走路也很快,上下班也是能走路就走路,"王金武笑着说,其实这也是他在繁忙工作中“挤”出来的锻炼之法。
每周二晚上,是雷打不动的研究生组会。在转化医学大楼的会议室里,灯光常常亮到深夜十一二点。王金武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这群同样拥有医学和工程背景的年轻人,热烈地讨论着最新的实验数据,或是某个注册证的审批进度。
从最初通过精细的手术做断肢再植,到现在通过生物打印机器人进行器官再造;从一个人在克利夫兰的孤独觉醒,到现在带领几百人的联盟团队集体突围;从只能跟着国外标准跑,到现在让世界参考中国标准。
从1989年那个想要经商的懵懂少年,到如今身兼数职的顶尖科学家,36年的时光,把王金武从微观的显微镜下,推向了宏观的产业变革潮头。
技术在变,角色在变,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
那个多年前在乡村诊所里,看着赤脚医生轻轻一托、让关节复位的瞬间,依然定格在他心里。
"希望通过我们医疗的发展,通过我们的技术,能有更加微创、更加精准、更加便宜的技术,为一老一小提供既有温暖又有人文、还有真正技术的这种治疗方案。"
这或许就是王金武心中,对于"医学"二字最朴素、也最宏大的注解。
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病人少受罪——这不仅是一位医生的初心,也是中国医疗创新的终极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