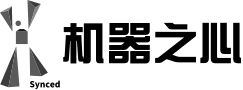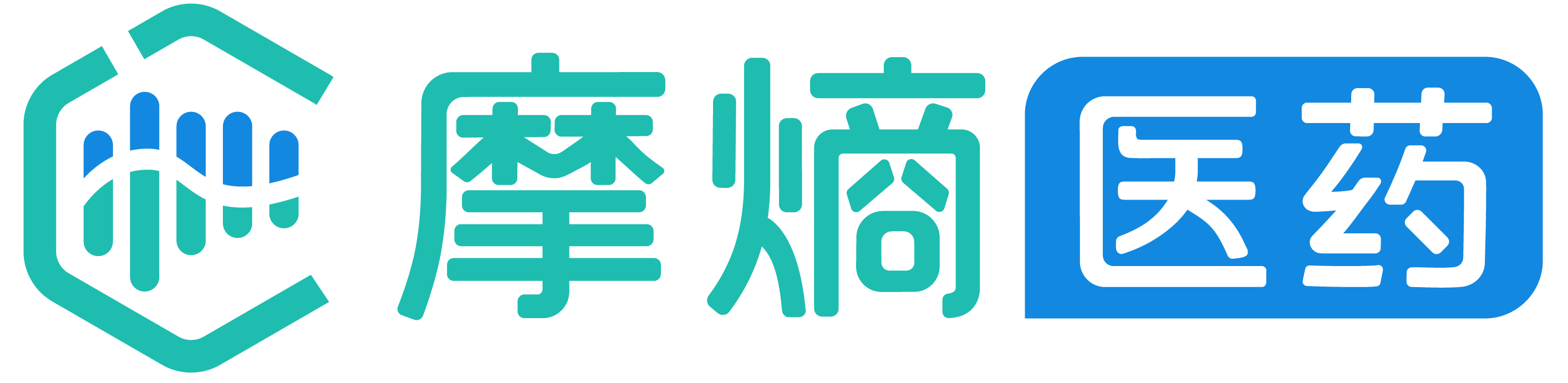尽管还没有完全征服病毒,但是人类对于病毒应用的探索却早已开始。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之一在实验室中摇身一变,化身成了传递DNA的运货车。
到如今病毒载体经过不断的设计优化,已经完全足以承载治愈疾病的希望。但从已经披露的信息上看,还有更多问题等待着解决。
药物递送并不是什么新话题。在小分子药物时代,递送通过剂型来实现。不同的剂型决定了小分子药物在何时被释放到何处,并因此决定了药物的给药量、给药途径和给药方式。
小分子药物稳定的理化性质使其不易在进入体内后被快速分解,容易触达起效部位,因此也不需要复杂的递送技术进行辅助。而在生物医药时代,生物药在产品“有效成分”的设计上更加贴近人体原本的生物学过程,但是想要将这些“有效成分”安全的送达起效位置,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病毒载体属于最早被开发的生物药递送技术之一。病毒载体的出现,最早主要就是为了解决DNA递送的问题。从20世纪后半叶,全球的科研机构就开始尝试通过病毒载体包裹遗传信息来彻底治愈遗传病。这一系列大胆尝试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项临床研究的积极成果来到顶峰。
199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William French Anderson医生领衔进行了一项长期临床试验,利用逆转录病毒将正常的腺苷脱氨酶(ADA)基因,递送到从患者体内分离的T细胞中,再回输到患者体内,用于治疗ADA缺乏性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症(ADA-SCID)的儿童。这项临床研究观察到了儿童症状的显著改善,William French Anderson也因此获得了“基因治疗之父”的称呼。在这项临床研究的鼓舞下,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基因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尤其集中在ADA-SCID领域。
虽然疗效摆在面前,但是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却没能让基因治疗的第一波浪潮一直持续下去。
1999年,一次严重的临床研究事故瞬间将这个领域打入了谷底。18岁的鸟氨酸转氨甲酰酶缺陷(OTC)患者Jesse Gelsinger在一项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中身亡。在这项临床试验中,研究者们尝试以腺病毒为载体将缺失的基因导入Jesse体内,但是腺病毒却引发了强烈的免疫反应,最终导致Jesse在接受治疗的4天后就因为多器官衰竭离世。随后FDA陆续关停了多项基因治疗的相关研究,这一事件也直接宣告了第一波基因治疗浪潮的终结。
我们如今再反观第一波浪潮,在这次对基因治疗的早期探索中,成也病毒载体,败也病毒载体。病毒载体在这次早期探索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后续病毒载体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逆转录病毒在这次浪潮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第一次表现出了随机插入的危险性。逆转录病毒的基础机理,是将目的片段以随机插入的方式整合到细胞的基因组上。这种随机插入插入带来的安全隐患在感染T细胞时并未表现出来。但当研究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干细胞阶段,安全隐患便被迅速放大。
2003年,5位接受了基因治疗的ADA-SCID患者被确诊白血病。他们接受的治疗中使用的逆转录病毒载体与William French Anderson当年使用的一样,都是莫罗尼小鼠白血病病毒载体。但是不同的是,William只对T细胞进行了改造和回输,而这五位患者接受的是造血干细胞的改造和移植。在治疗后虽然几位患者的免疫机能得到了明显的恢复,但是却因为逆转录病毒随机插入导致的LMO2异常激活而诱发了白血病。
再后来虽然研究者们对于莫罗尼小鼠白血病病毒载体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但是安全隐患却始终无法消除。时至今日,随即插入的风险仍然萦绕在逆转录病毒载体的后辈——慢病毒的头上。
而另一方面,十年浪潮的终结者,腺病毒则因为免疫原性过强和导入的环状DNA可能在细胞分裂中丢失而被腺相关病毒取代。后来又随着不断的开发优化,控制了免疫原性的腺病毒又在疫苗领域找到了自己的新应用场景。
在第一波浪潮的20年之后,随着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的快速兴起,病毒载体又一次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时下在生物医药领域应用的病毒类递送技术主要集中在慢病毒、腺病毒和腺相关病毒三个领域。
慢病毒是目前产业应用最成熟的病毒载体类型,尤其是在免疫细胞治疗,如CAR-T疗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慢病毒本质上是逆转录病毒中的一类,由于一般潜伏期较长,因此得名慢病毒。与其他的逆转录病毒类型相比,慢病毒能够能够穿透核膜,感染的更广泛的细胞阶段,对分裂细胞和非分裂细胞都能实现高效的感染。而大多数的逆转录病毒就没有穿透核膜的能力,只能等待有丝分裂时进入核中。因此在发展中慢病毒载体逐渐取代了原本的逆转录病毒载体体系。
目前常用的慢病毒体系仍然通过逆转录过程将目的片段整合到被感染细胞的基因组中。在病毒生产的过程中,表达外壳的质粒和搭载有目的片段的表达质粒被完全分割开,包装出的病毒不带有病毒外壳的基因序列,失去了复制的能力。因此常用的三质粒体系就已经有非常高的安全性,而后续进一步优化的四质粒体系则更加安全。
整体上来说,慢病毒感染体系完整保留了原本逆转录病毒高表达效率和长表达时间的优点,并且在感染能力上有了巨大的提升。目前的CAR-T产品就使用了以慢病毒为主的感染体系来实现T细胞中CAR的表达。从目前为止的表现上看,CAR-T发生的部分安全性问题都与慢病毒的使用无关。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慢病毒体系的绝对安全。慢病毒在继承逆转录病毒有点的同时,也继承了其随机插入的不稳定性。与20世纪末的情况一样,当研究深入到干细胞层面时,随机插入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在所难免。
2021年2月,Bluebird用于治疗镰刀状细胞贫血症(SCD)的产品LentiGoblin发生了安全性问题,在该产品的1/2期临床研究中,有两名患者分别确诊了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和骨髓细胞异常增生症(MDS),导致该药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也因此宣布暂停。这一事件同时也影响到了Bluebird的其他产品。其已经上市的Zynteglo因为与LentiGoblin使用了同样的慢病毒载体也因此被暂停销售。
Bluebird并不是不幸遇到安全性问题的唯一一家,另一家罕见病药物研发企业Orchard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问题。Orchard在2020年10月披露,其收购自GSK的Strimvelis可能导致了一名患者的白血病。Strimvelis最早在2016年获欧盟批准,用于ADA-SCID的治疗。在这次事件之后,Strimvelis的销售自然也被暂停。
同样是逆转录病毒(慢病毒),同样是造血干细胞,同样是血液瘤,这种随机插入带来的安全性问题时隔20年再次上演,可能真的代表着慢病毒在遗传性罕见病的根治上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但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这些选择了基因治疗的患者,大多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骨髓配型而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那么一个两难的抉择就摆在这些患者面前,究竟是选择继续忍受疾病的折磨,还是拼着患上血液瘤的风险给自己一个痊愈的机会?使用慢病毒递送技术的血液病治疗方案可能真的有无法避免的风险,但它至少给了这些患者一种选择。
在腺病毒终结了第一波基因治疗的浪潮之后,这种病毒载体并没有因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在持续不断的优化过程中,腺病毒的免疫原性逐渐降低,目前已经基本可控。只不过在很多原本使用腺病毒的场景中,人们发现腺相关病毒的效果更好,安全性更高,因此在基因治疗中更多的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载体。
但是腺病毒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相比于慢病毒体系,腺病毒搭载的基因导入后并不会整合到基因组上,因此不会有随机插入的风险;腺病毒载体的包装容量也是几类病毒载体中最大的,最高可以插入7.5kb的外源片段;并且腺病毒载体的感染效率非常高,感染后的表达速度也很快。
基于这些特点,腺病毒很快在疫苗领域找到了自己的新应用场景。腺病毒疫苗相对研发生产过程简单,可以在注射后的短期内大量表达抗原蛋白,并在一段时间后随着细胞的分裂和复制被代谢掉。
在新冠疫情中,康希诺生物、阿斯利康和强生都选择了腺病毒载体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腺病毒还是出现了安全性问题。强生和阿斯利康的疫苗都屡有安全性问题爆出。康希诺生物的疫苗是三款产品中安全性表现最好的一款,基本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发生,但是接种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显著高于广泛使用的灭活疫苗。因此腺病毒载体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未来可能还需要继续优化载体的安全性。
随着几款基因治疗产品的相继获批,腺相关病毒(AAV)作为新型病毒载体递送技术被一再提及。而AAV的安全性和临床价值也在这些产品的临床使用中被展现。
相较于腺病毒,AAV解决了腺病毒最大的问题——免疫原性。AAV的免疫原性很低,而且几乎没有对人的致病性。这也就代表着AAV载体的使用不会引起严重的免疫反应,并且其保留的病毒结构不存在致病性,使得AAV载体的安全性大幅提高。
并且当前使用的AAV载体已经失去了野生型AAV整合到基因组上的能力,导入的片段通过首尾相接的环状DNA形式存在于细胞核中,又进一步提高了AAV载体的安全性。
不同血清型的AAV载体因为衣壳蛋白的不同,对不同组织和细胞的转染效率存在差异。通过选择合适的的血清型的AAV载体,还能实现对不同组织器官的精准递送。
当然AAV载体的弊端也比较明显,一是载体容量比较小,二是感染到表达的时间比较长。但这些缺点目前还没有制约到AAV载体的产业应用。
已经有几款使用AAV载体的药物相继获批。2012年获欧盟批准上市的Glybera是第一款获批的AAV药物;随后在2017年,美国FDA批准了Spark Therapeutics的Luxturna上市;2019年美国FDA又批准了诺华旗下AveXis的Zolgensma上市。
如果说这三款产品有哪些共同点,除了用了同样的递送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贵”。这三款药物的价格都堪称天价,Zolgensma的定价达高达212.5万美元,是目前为止最贵的药物;Glybera则因为定价过高无人使用,而最终黯然退市。
一款产品的定价要综合考虑到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广费用、已经花费的研发费用,适应症群体等多个方面。我们并不想在这里过多的探讨有关商品定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导致这些产品最终定出天价的原因中,AAV载体的生产成本并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而且从目前为止几款产品的表现上看,AAV似乎非常契合这一应用场景。
以上的三种病毒载体,在国内虽然还没有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是已经有大量基因与细胞治疗的企业有相关的布局。实际上除了少量以电转的方法实现递送的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的基因与细胞治疗的企业都必须要面对病毒载体的研发问题。
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谈到的,腺病毒载体目前主要应用于疫苗领域;慢病毒载体主要应用于细胞治疗;AAV载体则主要应用于基因治疗。抛开应用并不算多的腺病毒不谈,慢病毒载体和AAV载体由于其应用场景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成熟度在国内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区别。
近两年由于细胞治疗的大火,慢病毒的相关产业化发展的非常迅猛。慢病毒的研发设计、加工生产,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SOP体系,并向外延伸,促成了细胞治疗CDMO产业的快速兴起。
另一方面,AAV的研发外包产业也已经出现苗头,但由于产业发展相对早期,目前行业内的还没有明确的共识。如何完善AAV载体的GMP生产,仍然是很多基因治疗企业的关注重点。
动脉网联同盛山资本和自贸壹号,推出线下系列沙龙【思享会】第35期。与会的各位大咖们将围绕着病毒载体的基因药物开发,探讨行业发展,品读核心技术。扫描下方图中二维码即可立即报名。